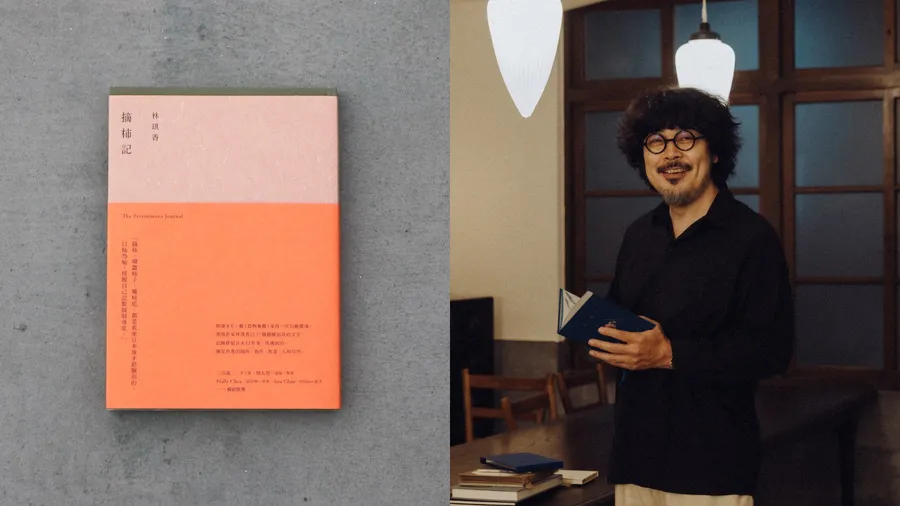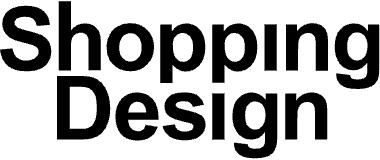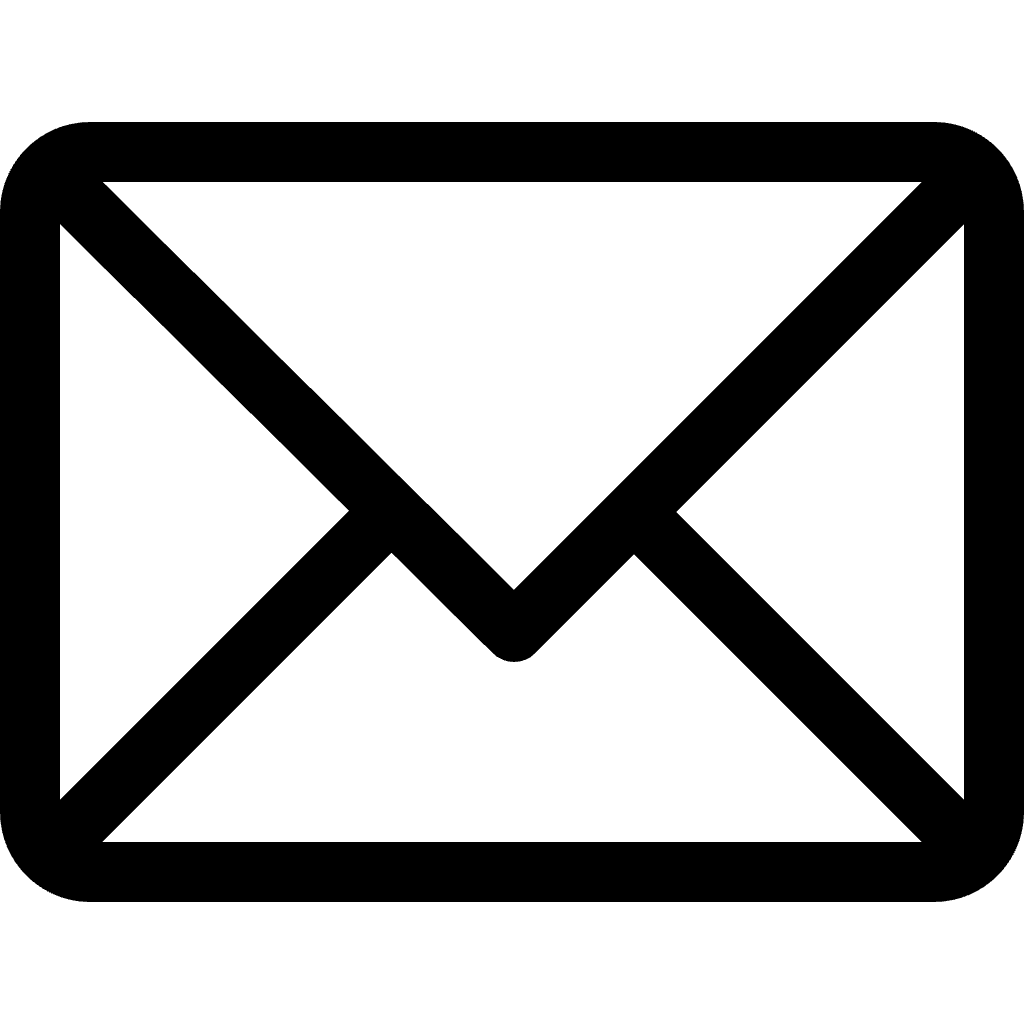2014 年,畢業於紐約 Pratt 及 Parsons 設計學院的逸寧結束了 8 年的旅美生涯,回到台灣,重新摸索台灣設計產業生態。
「可想而知,那個時候台灣設計產業普遍待遇不盡理想,因此當時的我幾乎可以說是且戰且走,」逸寧笑說,回國不久,便接到高中社團朋友張雲淞的邀約,說他們正在籌備一間新創公司,「因為在紐約的時候,也參加過多家新創公司的草創,因此當時張雲淞找我的時候,其實我並沒有想那麼多,就覺得是幫朋友忙,新創公司嘛,也許很快就會失敗了。沒想到這個忙,一幫就是八年。」
2014 年,張雲淞創辦了小樹屋的前身 Pickone 挑場地共享空間租借平台,身兼共同創辦人及品牌長的黃逸寧也一頭洗了下去,一路走來,辛苦有時、快意有時,不知不覺,小樹屋也已經在台灣共享空間市場打出了不小的名號。
逸寧說,帶著藝術及工程設計的背景加入團隊,面對房地產及共享空間這個龐大且未知的領域,設計師職能帶領她前往的,是一場驅動改變的旅程。
關於設計與商業、商業與設計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逸寧笑說,這八年已有深刻領悟,兩者之間密不可分,就如同左腦與右腦之間,永遠都要保留對話的可能性,設計師的商業晉級之路,繼續走下去,才能看到右腦看不到的風景。
想聽逸寧分享「空間加值生活:以城市一隅打造「屬於你」的空間體驗」,歡迎👉 報名 12/10 DesignBIZ Stage 靈感設交場,帶你悠遊設計的商業場景,進入靈感心流,探索未知的遠方!
∷ Podcast「設計關鍵字」by Shopping Design
☊ 點此收聽 ⧸ 小樹屋共同創辦人暨品牌長 Podcast 完整專訪
小樹屋以「設計」開放空間使用的可能性
SD:從設計領域跨足商業場景,過程中曾經遇過哪些困難?
黃逸寧:最大的困難在於覺得別人都不理解我(笑)。我始終認為,設計及美感有其價值,但約莫 6-8 年前,我發現自己很難去說服別人,它為何重要?
對於設計師而言,「溝通力」始終是職涯的關鍵,首先得學會如何換位思考,去理解商業世界如何運作,以及設計它如何被商業所需,如此一來彼此溝通才有可能在同一水平線上,以促成雙方都滿意的成果。
小樹屋在 2014 年創立時,當時大環境對設計的要求相對簡單,只要把平面視覺做好,足以延伸到多個接觸點,使受眾感受到這個品牌有完整的視覺呈現,就足以與市場上其他的品牌做出區隔;然而現在無論是做品牌,還是產品,都不能僅停留在視覺的表面,需要更往內在精神層面去探索。
以小樹屋的空間來說,我們開始需要思考,每一個不同的共享空間設計,它的擺設、場景、動線是否能夠更加豐富,可對應各種類型使用在多元化的需求;同時,建築物的多元性也開始增加,從過去的商辦大樓,到現在陸續開始執行、接觸老屋改造的案子,以及小樹屋電話亭的延伸,對我們來說都是在回應使用者在不同情境上的需求。
多元的意思是,不只給單一目的,而是將空間開放出來,歡迎使用者發揮創意,觀察自己生活中,有哪一時刻是可以被放到這樣的空間來去實踐?
老屋的重建與新生:保留歷史軌跡,注入創新元素
SD:當初接下大千百貨時,如何去想像古蹟的使用場景?
黃逸寧:大千百貨座落在南京西路及延平北路口,那一處是直至台灣光復時期,仍商家林立、街屋成群的繁華地帶,而這幢可以說是 1970 年代「最時髦」的摩登百貨就蓋在那裡,然而隨著大稻埕街區的沒落,大千百貨也逐漸沉寂下來,於 1990 年左右歇業後,2005 年被台北市文化局登錄為歷史建築,持續經過幾次翻修,才有今天的模樣。
小樹屋團隊承接這個空間之後,也做了相當多的功課,包括實地走訪大稻埕附近街區,去了解大千百貨發展前後的歷史,發現這幢房子座落在這條街上,經歷時代的更迭,本身就擁有相當飽滿的故事,包括它在日據時代曾經是棟旅館,中途經過戰亂,於 1970 年代由大千百貨進駐,輾轉經過幾手,最後才經由現任房東,來到我們手上。
當初在想像這個空間時,我們最大的共識,是盡可能地保留這整段歷史,透過古蹟的年代感、氛圍感去傳遞它的魅力。
因此在設計方面,團隊並沒有加入太多複雜元素,去掩蓋掉它既有的樣子,牆上因為歲月而留下的斑駁痕跡,裸露的建體結構都刻意地被我們保留下來,以襯托的方式將它重新包裝,期待讓更多年輕人可以認識這棟房子。
事實上,要年輕人百分之百接受九O年代的東西仍有它的難度,因為建築體它本身肯定具備當代的文化及美學脈絡,因此我們採取局部設計的方式,將一些小的設計元素放進去,襯托原先建築體及內裝年代感的同時,又與當代年輕人喜歡的元素呼應,彼此之間取得平衡,才有了現在大家所看到的「紅豆杉」。
相較於其他老屋改建的場域,例如旅店、咖啡廳,小樹屋作為一個共享空間的平台,會更期待賦予古蹟空間「開放」與「共享」的可能性。以老屋咖啡廳為例,用戶的使用行為多半是「被設定好的」,你必須在某特定時間,不預期地與不特定人共享該空間氛圍,在行為與移動範圍皆有所限制的情況下,其實很難與空間產生真實的互動。
小樹屋不同之處在於,它以「小時」為單位租借空間,用戶租借多少「小時」,在這段期間,這個古蹟空間的擁有者就是該名使用者,並且能夠自己決定如何與這個空間互動,小樹屋透過此種共享模式,讓古蹟空間利用的可能性延伸出去,在租借時段裡開放想像、自行配置。
新創的品牌經營心法?以「精神」貫穿產品!
SD:你如何看待「設計」與「商業」之間的關係?
黃逸寧:我想無論在什麼產業,包括小樹屋所在的房地產及共享空間產業,設計都是相當重要的一塊。
由於我自己是設計背景出生的,過去這 8 年期間,在團隊中也持續擔任將設計帶進來的角色,即便過程經歷許多摩擦,但也希望透過這些來回的辯證,能讓更多人知道——透過設計,能夠更精準地傳遞品牌所欲傳達的訊息。
設計不只是一項美感的專業,它更像是針對一個問題,提供系統性的解法。
我自己認為,設計要想進入商業場景,設計師首先要先理解對方究竟在想什麼,這個產品、服務或空間期待訴諸什麼樣的感受?如此一來,才能在達成商業目的的前提之下,讓設計思考得以延續,並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將品牌想傳遞的訊息,順利地傳遞出去。
透過設計,可以讓品牌精神像水一樣地流淌到各個地方。
面對「設計」和「商業」之間的配合與拉扯,有時候就像左腦與右腦間的協作。在創業初期時,創意人的跳耀性思考常常會跑出來,讓我很常在自己的邏輯裡面,同事們很難接住我想要講的東西,我相信具備藝術家性格的人多多少少都會有這樣的狀況,對我來說最好的解決方法是不斷地練習,首先透過換位思考,去理解對方需求,再回過頭來自己爬梳自己的思考脈絡,透過書寫或是文件的方式記錄下來,也能夠一定程度地幫助我們線性思考。
SD:小樹屋當初建立品牌部門的契機為何?如何定義這個品牌?
黃逸寧:其實公司建立前 4-5 年都沒有成立品牌部門,跟很多新創公司一樣,公司成長到一定的時期,劃分部門的時候,就發現我要做的某些事情,既不能被歸類到「產品」,也不能歸類至「營運」,更不是所謂的「技術」。那麼這些事情到底是什麼?到底該由什麼樣的部門統籌?
細細推敲、分門別類下來,才發現我們好像需要一個「品牌部門」。
至於究竟什麼是「品牌」,當初也只是非常攏統的、模糊的定義,去判斷品牌也許包含清楚的識別,或是企業的某種精神方向。
我相信一定有非常多的品牌在創業初期遇到和我們一樣的困境,在本質上,公司其實並沒有導入任何的品牌思維,而是誤將平面設計的概念視為「品牌」,以為我把 logo 做好、家具選好、空間建置完善,那就是品牌了。
品牌被賦予的使命,是希望把上述所有的一切都再提高一個層次,也就是相比於看得到、摸得到以及實際能夠過價值衡量的東西,品牌更在意的是精神價值。
透過空間去承載這些不同可能性,讓使用者的生活更有彈性,才是小樹屋期待在市場發揮的影響力。從產品的推廣,到「新生活態度」的推廣,這段路程,小樹屋走了八年,我們才開始意識到說,我們期待的,是有越來越多人願意選擇在小樹屋完成他人生中好幾項最重要的大事,例如告白,例如求婚,又例如同學會。
SD:過去 8 年,觀察台灣整體設計生態有何改變?
黃逸寧:其實設計是非常邏輯的一件事情,他不只是視覺的東西,美學素養是這之中最基本的條件,但某種程度上,最基本的也最珍貴,最珍貴的也就最困難達成。
美學素養和文化底蘊有關,而文化就包含整體環境。即便很多人都會說「國外的東西比較美」,我仍然認為台灣也有其獨特的美感,在歷史及文化脈絡種種因素之下,台灣基本上是一個多元文化的載體,畢竟它在短短的時間內,經歷相當巨大的認同轉移,台灣人雖然最為一個「集體」的代稱,但是每一個人對於自己的身份認同皆有不同,台灣是多元集合的島嶼,因此我們比較難有強烈且一脈相承的文化底蘊,或者是集體認同感。
但在這種情況下,要去把美感設計集結起來,我認為確實相當具有難度,且有挑戰性。
即便如此,我認為小樹屋看待「設計」這件事情的使命,便是在這些多元且複雜的元素之中,找出一個或多個共通點,將當代台灣人認同的語彙加進去,然後共享給所有人。
黃逸寧|Happ. 小樹屋 / 共同創辦人暨品牌長
畢業於紐約 Pratt 以及 Parsons 設計學院。曾以藝術家之姿創作、參展,也曾於美國、台灣參與多家新創公司的草創。現今帶著藝術設計與工程的背景加入共享空間的產業,在創業過程中,以跨領域的經驗串聯起設計與商業。